不想去养老院的独居老人,如何体面老去
- 科创板分析
- 2025-04-18 08:58:04
- 12

上海的长护险和 " 家床 " 服务的配套进行,也给了全国探索养老照护和相应制度一些启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以及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瓦解,单身或丁克成为年轻人的选择之一," 养老社会化 " 是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许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作者 | 顺顺
编辑 | 陆一鸣
题图 | 《郊游》
走进上海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瞿溪路某小区,一位老人独自倚着辅助架慢慢地走着,时而停下来喘口气。低矮的居民楼门口,有老人正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眯缝,仿佛时间停滞。这是上海市中心居住区给人的感受,房子很旧,老年人也很多。

上海市中心某小区。(图 / 作者摄)
根据上海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末,上海市 65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到 437.9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8.8%,意味着深度老龄化的到来。同一时期,上海全市 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为 81.64 万人,其中全部人口都在 80 岁及以上的 " 纯老家庭 " 人数为 33.10 万人。
当你老了,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将如何度过?这是每个人终将面临的问题。
近些年来,在政策和社区的推动下,上海有不少养老机构逐渐将长护险落地,让一部分失能或者超高龄老人享受到照护,同时慢慢开展 " 家庭照护床位 " 服务,将养老床位搬进家庭,从 2019 年开始,上海开始探索这种 " 家床 " 新模式,首批试点已经在黄浦、静安等区开展一段时间。
未来," 居家养老 " 的愿望真的可以实现吗?

一个人在熟悉的房子里老去,可能吗?(图 /《郊游》)

93 岁,在家独居养老
戚奶奶今年已经 93 岁了。老伴去世后,她一直独自待在这个一室户的房子里,一个人的生活,她已经过了三十多年。见到戚奶奶的那天,天气有点阴,她的房子位于三楼,采光并不太好,但是她的家井井有条,散发出干净的经常通风的味道。
她家的小沙发后面,挂着一张大的照片,是九十岁寿辰时,她的孩子请人拍,照片中,戚奶奶笑得慈祥平和。
两年多以前,她得了肿瘤,动了一次大手术,手术后很长时间都需要人照顾,再加上她腿脚慢慢变得不灵活,上下楼走动变得困难。一般情况下,这么大年纪,一个人住也许不是最合适的选择。孩子们希望把她接过去住,但她拒绝了。" 房子再大我也不要,一个人住自由 "。

戚奶奶家里的一面橱柜里,是她收集的各路神仙。(图 / 作者摄)
或者去养老院是另一种选择,有专门的人照顾起居。但她也不喜欢养老院。这时候她突然偷笑," 我睡懒觉 ",她一般晚上十二点才睡,吃上医院配好的安眠药,早上睡到八九点钟。但是在养老院就不能这么随性了,在家里,她可以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问她日常都怎么度过,她说 " 看看窗外,再看看屋子里 ",在她的家里,几盆花被照料得很鲜翠,她说那是孙女买来的,桌上和落地柜上堆着一些看过的报纸,平常,她还喜欢养些小昆虫。
她讲起在这个街区生活了六七十年了," 以前这里是垃圾地方 ",她说,周围都是卖棺材的,谁知时代变迁,现在这块地成了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年轻时候,她做财务,也见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的腾飞。那时候她经常需要经手大量现金并代为保管,不仅走在路上害怕丢了,放在家里也担惊受怕,因为没有保险柜。
如今,虽然已经远离了财会的工作,戚奶奶却保留下了打算盘的习惯。在她柜子里有一个木制的算盘,上面都是她飞速拨动珠子留下的划痕,或许正是这样的习惯,让她得以在九十多岁的高龄仍然保持着灵活的思维。

戚奶奶的算盘。(图 / 作者摄)
女儿和孙子们都搬离了这个地方,她讲起自己那 " 到处飞来飞去出差 " 的出息的孙女尤为满意。在这个小区里,她还认识的老邻居也只剩下两位,但由于腿脚不灵活,她也很少出去串门了。在她的人生里,似乎从没想过要去规划养老生活," 都是顺其自然 ",等到不能做饭洗碗了就请保姆。
直到两年多前,在动完那个大手术后,戚奶奶突然不能再独自料理生活。在社区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评估下,她获得了长护险的资格,有人会定期上门来帮她打理一些生活需求,包括洗头、洗澡清洁等服务。
所谓长护险,是指为失能人群提供护理服务或资金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自 2016 年以来,我国先后在 49 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上海是其中执行得较好的城市之一。
不过,长护险的评估条件比较高,目前只有失能或者半失能以及特殊情况的高龄老人才能通过评估。对上门服务产生的费用,长护险基金报销 90%,个人承担 10%。通常照护员每小时收费 65 元,这其中,被护理的老人每次只需支付 6.5 元,剩下的 58.5 元则由上海长护险基金支付。
此外,戚奶奶还在享受一项 " 家庭照护床位 " 的服务。比起长护险的社会保障性质," 家床 " 服务一般由机构承担,意在将专业照护服务延伸至老年人家中,目前在上海黄浦区和静安区有几十个机构提供 " 家床 " 服务,同样也是由机构的养老评估人员上门评估老人需求,定制合适的服务。
戚奶奶说,有时候一个人待着也会孤独,有人上门来聊聊天她也挺乐意,照护师小李成了她平常聊天的对象之一。小李是上海提供 " 家床 " 服务的机构之一福苑养老的照护师,大约 40 岁,看起来很年轻,我们刚到奶奶家的时候,小李刚帮奶奶做好了一些家务,并做了简单的身体护理——揉揉肩膀、剪剪指甲,一切都看奶奶的需求。

在护工的照顾下,老年人得以在家里更舒适地生活。(图 / 纪录片《前浪》)
奶奶和小李已经认识一年多了,她很喜欢小李,有时候需要的话,还会直接拿钱让小李帮忙买点东西。小李性格温和,总是笑着,在奶奶家服务完了,她还要赶去下一个家庭为老人服务。
福苑养老的照护经理牛国帅说,长护险规定的服务次数和服务内容比较有限," 家床 " 服务则弥补了长护险覆盖不及之处,比较灵活,比如可以帮老人做保洁、烧饭等。现在,戚奶奶的三餐由社区的长者食堂提供送上门服务,有时候也可以让小李帮忙烧饭。
同时," 家床 " 服务也给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熟悉的照护人员。自家雇请的保姆一旦辞职或者请假,又得重新找人,在年节时段返乡高峰期尤其如此,但 " 家床 " 服务则可以马上调配人替补。

小区里的老人开着助步车。(图 / 作者摄)

人可以在熟悉的家中老去吗?
牛国帅在从事养老行业之前是一名护士,2018 年的时候他从医院辞职,彼时上海刚好在推行长护险的养老保障政策,他误打误撞加入了养老机构,并主要做长护险相关的工作,之前做护士时的工作训练让他可以顺利过渡到养老服务中。
随着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们的养老需求越来越大,有些人更愿意在熟悉的环境里待着," 家床 " 养老服务也应运而生。牛国帅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上门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等匹配相应的 " 家床 " 照护项目。

" 家床 " 照护师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图 / 受访者供图)
在从事多年的上门养老服务中,牛国帅的经验是,这些家庭中,有 90% 是纯老家庭(养老行业的术语,意为只有老人居住的家庭),孩子成家后一般都不与父母同住,纯老家庭中还有大约三分之一是老人独居的情况。
在上海从事养老行业的这些年里,最让牛国帅感受到冲击的还是上海人的养育观念。他的老家在河南,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孩子 " 孝顺 " 天经地义,但他接触的许多上海老人中,很少有人会抱怨孩子不孝顺," 他们不太依赖子女,也不认为老了就要孩子来养,更享受养育的过程 "。
牛国帅说,许多老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养老院,也有老人进去养老院之后又搬了出来。在一个地方同吃同住、到点吃饭,让他们很不习惯。
日本知名学者上野千鹤子也在多本关于养老的书中表达过自己对于住养老院的抗拒。《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一书中,她写道," 不管是养老机构还是日托中心我都不想去 …… 去日托中心,就像小孩子被送进托儿所一个道理 "。在养老机构,人们的 24 小时生活起居都在里面进行,这对年轻时候就不喜欢集体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问题。

作者 : [ 日 ] 上野千鹤子
出版社 : 译林出版社
牛国帅说,正是因为老年人不愿意住养老院,才会出现 " 家床 " 服务,机构再根据老人的不同需求,去匹配做饭、清洁、修理、身体护理等服务。从去年开始,在街道社区的牵头下,牛国帅所在的机构福苑还面向年龄偏大或者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推出了 24 小时应急响应的服务。
养老机构在每个街区设置了 3 个点,每个点位都有 24 小时值班人员,可以在 15 分钟内赶到事发地点为老人提供紧急协助。从去年到现在,一共有 6 起服务事件被触发,都是在夜间。
牛国帅说,有一起事件发生在凌晨一点多,两位老人都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阿婆起夜的时候,突然感到天旋地转,还伴随着呕吐的感觉,阿婆原本就患有严重高血压,老伴也行走不便,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下拨打了 24 小时应急响应的热线。
接到电话后,站点工作人员 10 分钟内就赶到了老人家里,帮忙叫了 120,并陪同老人到医院,帮助阿婆挂号、做检查、拿报告,同时通知老人家住青浦的女儿,大概两个小时后,老人的女儿从郊区青浦赶到,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是一位独居老人自己在家里吃了缓解便秘的药,结果变成了严重的腹泻,最后搞得全身上下都脏了。因为腿脚没有力气,老人甚至自己无力处理,只好拨打了应急电话,工作人员马上到家帮忙处理了。牛国帅说," 这种情况不算紧急,但还是很有必要帮忙处理 "。涉及老人的尊严,紧急响应也很有必要。也有老人晚上起夜时候,发现马桶往外溢水,一个人手足无措,他们也会上门提供帮助。

看见老年人的需求。(图 /《今日公休》)
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和需求," 家床 " 服务也会上门给一些卧床老人安装监控或者应急报警装置。人到晚年就是一个身体逐渐衰退的过程,牛国帅说,老人到最后如果坚持要在家里养老,就需要一个 24 小时住家的照护师,这样在家里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背后还有一个养老院的资源支持,比如团队还会有护士定期上门给老人量血糖血压、检查吃药状况、做基本的生命体征监测,并做出及时就医的建议。
从 2022 年开始,上海静安区开始试点一项 " 五床联动 " 的服务。" 五床 ",即家庭照护床位、养老机构床位、家庭病床、医疗病床(区内一级、二级医院的治疗病床)和安宁疗护病床。" 五床 " 之间建立一个绿色通道,形成资源共享。
当一个老人的身体状况发生改变的时候,在专业人员评估后,可以通过绿色通道到医院进行诊疗,或者判断是否进入照护中心进行特殊照顾等,甚至是到了老人临终时,也可以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入住安宁疗护病床。
通过家庭养老床位与养老机构床位、医疗机构床位之间的互转,老人得以实现在熟悉的环境中度过晚年的心愿。

让老年人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度过每一个环节。(图 /《桃姐》)

不再害怕老去的社会
牛国帅说,像戚奶奶所在的五里桥街道,是 " 家床 " 等服务对老年人补贴力度较大的区域之一。目前 " 家床 " 有 30% 左右的补贴,之后逐渐递减,到期之后完全自费。目的是引导老人感受这个服务,最终尽量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的需求。
福苑官网的收费显示,一个老人如果需要在 " 家床 " 服务中请一个 24 小时的照护师,每个月至少支出 6500 元,与进普通养老院的价格大致相当。能否负担得起,除了特殊政策补贴,还取决于老年人的退休金。
不过,在上海," 家床 " 服务有大量市场潜力,许多有支付能力的老人还从未听说过这项居家养老的服务,养老机构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先让这部分老人能慢慢了解并接受这项服务,让这一模式运转起来。

照护师为老人剪指甲。(图 / 福苑养老)
上海的长护险和 " 家床 " 服务的配套进行,也给了全国探索养老照护和相应制度一些启示。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人口老龄化的深化以及传统家庭结构的逐渐瓦解,单身或丁克成为年轻人的选择之一," 养老社会化 " 是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
老龄化情况出现更早的日本社会,相关措施或许值得参考。《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中,上野千鹤子对日本的医疗、看护、护理等最新情况全面调研,也分享了自己为晚年独居生活所做的准备,给了人不少 " 别害怕独居老去 " 的信心。除了讲述 " 居家养老 " 的可能性,上野千鹤子也分析了日本 " 养老社会化 " 的制度基础。
日本从 2000 年开始实施的 " 介护保险 " 制度,与中国目前正试点实施的长护险有相似之处。所谓介护,包含对失能或者半失能的人们有入浴、排便、饮食、机能训练和护理,甚至医疗的需求的保障,只要通过评估,40 岁以上的日本人或者在日外国人都可以是介护保障对象。

日本介护制度,已经实施了二十几年。(图 /《0.5 毫米》)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这项保险制度和日本其他国民社保一样,都以员工、企业和政府补贴共同筹措资金。为了保证公平,个人缴纳税款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在保险范围内,一个需要介护的人只需要承担 10% 的费用。
介护保险制度实施十余年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社会养老模式由家庭化向社会化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度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日本刚开始实施介护保险时,整个日本社会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但介护保险的强制征收,无形中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养老市场,促进了养老产业的专业化。
目前的中国也正处于一个养老制度和产业专业化探索的初步阶段。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副主任于洋在 2024 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全面推行长护险的现状下," 我国仍面临着护理服务供给不足,即护理人员的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低、护理机构发展缓慢等困难和问题。" 此外,中国还面临人口规模庞大、城乡差距大、财政支出不足以负担等问题。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衰老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失能、失智的状况也时有发生,比起恐惧和排斥,建设一个即便需要护理也能让人感到安心的社会,一个即便失能、失智也能有尊严生活的社会,是一个艰难但同样重要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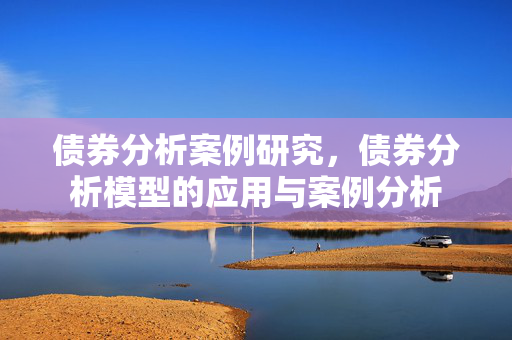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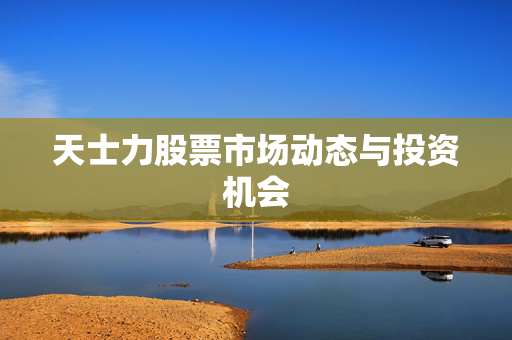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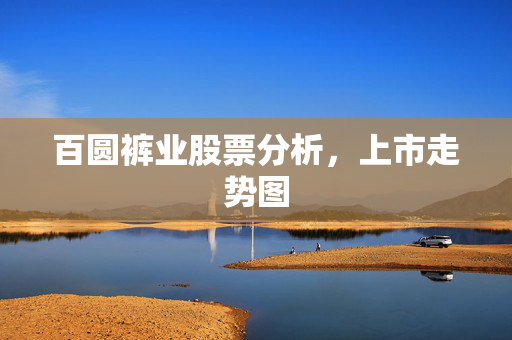







有话要说...